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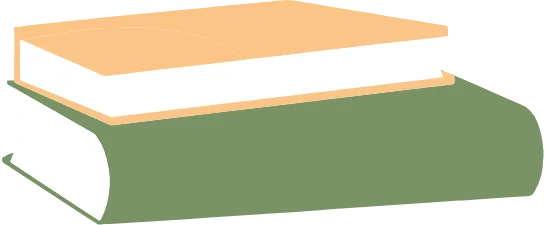
钱穆先生作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,其代表作《国史大纲》是抗日战争战火中各个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,详于阐述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文化、制度,对于具体的人与事则一略而过。而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可以说是《国史大纲》的进一步延伸,通过对中国古代汉、唐、宋、明、清等五个朝代政治制度的深入分析和比较,试图揭示政治制度背后的逻辑和规律,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。“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”,国浩深圳合伙人李芳对此书进行了细读,并摘其精要,与大家共享。

“以铜为鉴,可以正衣冠;以人为鉴,可以知得失;以史为鉴,可以知兴替。”
近几年来一直在零零碎碎地读些历史,感觉历史中间自然蕴藏着它不可言说的力量。但是贸然读史,总有一种无从下嘴的感觉:读历史时我们到底需要关注什么?我们能够从哪些角度来观察历史?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学习什么?
正当笔者在历史的迷宫前茫然不知所措时,钱穆先生适时出现,像一个导游,用他的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一书,把自汉代至清代的政治制度梳理了一遍,从政府组织、选举制度、经济制度、兵役制度四个方面,分析汉、唐、宋、明、清的制度利弊。王朝间的兴替、兴替中的传承、传承下的变革,俨然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,在眼前徐徐展开。全书都很精彩,不再一一复述,只能摘出阅读过程中笔者感触颇深的几个片段,与大家分享。
(注:文中加了引号的内容,如果没有注明其他出处,那就都是引用钱穆先生在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一书中的表述。)
一
汉武帝把盐铁经营权收归国有
商业要对自己的政治地位有清醒的认识
话说当年,汉武帝为了开疆拓土,预算不够用了。汉武帝把自己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,发现还是不够用。于是号召地方上的有钱人,尤其是收益颇丰的盐铁商人,给国家捐些钱,以便汉武帝能够继续完成自己的宏伟大业。
但是,响应者却寥寥无几。
汉武帝就怒了,怒的同时脑子还在线,他就想啊:你们盐铁商人赚这么多钱,到底是从哪里赚的呢?
“岂不是都由我把山海池泽让给你们经营,你们才能煮盐冶铁,发财赚钱”,钱穆先生在书中是这么描述的,“现在我把少府收入都捐献给国家,而你们不响应;那么我只有把全国的山海池泽一切非耕地收还,由我让政府来经营吧!”(少府收入就是汉武帝的皇家私房钱)
于是乎,盐铁经营权自此收归国有,商人们不能再擅自经营。这项制度一直传承至今,迄今《民法典》物权编里仍然明明白白写着,“矿藏、水流、海域属于国家所有……城市的土地,属于国家所有……森林、山岭、草原、荒地、滩涂等自然资源,属于国家所有”,属于集体所有或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这些归国家所有的资源,商人们想申请经营的话,都是需要办理行政许可手续的。
汉代的盐铁商们为什么会是这个局面?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地位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。国家政权站在一个国家的食物链顶端,对一国政权中的活动享有绝对的话语权,商业活动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体量够大,就能够与一国政权相抗衡。
远的不说,近的就有好多鲜活的例子,这里不再一一列举。只能说:不论是在哪国经商,商业群体都需要有足够的政治敏感性,以及合适的政治观念。
二
皇权和相权的分割与制衡
分权这件事情不是西方才有
(一) 皇权中分化出相权,并相互制衡
一说到分权,我们往往把目光看向西方,提及洛克、孟德斯鸠,并对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津津乐道。但其实早在中国汉代,就有了自成一家的分权思想和制度,那就是皇权和相权的分割与制衡,以及对相权的进一步分割和制衡(汉代从秦朝传承下来的三公制度,唐代的三省制度)。
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,中国历史上形成统一政府始于秦代,汉代则把这一制度传承并发扬光大。而皇帝作为一国政权的领袖及代言人,他的诞生孕育了皇权这一权力形态。
但皇帝一人及皇室的力量有限,不能以一己之力完成整个国家运行管理的繁重任务,所以需要帮手来帮他打理家国事务。这个帮手从哪里来呢?
自然是“亲中选贤”:秦汉形成统一政府之后,化家为国,皇帝的家臣们也一跃成为国家机构的管理人员。
基于此,汉代的各类官名,都是始于前朝历代对家臣的称呼:宰(内管家)、相(副手)、太常(即“太尝”,试菜有没有毒的)、光禄勋(看门的)、卫尉(保安队长)、太仆(赶车的、司机)、廷尉(执行家法的)、大鸿胪(传话的)、宗正(修家谱的)、大司农(管钱的【皇室外经济】)、少府(管钱的【皇室内经济】)。(这就是汉代九卿在当时的真实含义,跟“弼马温”之类的称呼,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。)
扯远了,言归正传:皇帝需要从自己的家臣中选帮手来打理家国事务,并形成了政府组织。而宰相作为政府组织的首脑,就带来了“相权”这一权力形态。
相权既是皇权的辅助,也是对皇权的制约,皇权和相权自其诞生时就自带相互制衡的属性,因为相权背后的文官集团的力量,也是不容小觑的,不是非常有个人魅力的君王,很难周全应对。当年万历皇帝因为疲于应付文官集团,索性二十年不上朝。一山不容二虎,皇权与相权在中国历史上,开始了他们相爱相杀的旅程。
(二) 皇权对相权的兼并
按中国历史的总体趋势来看,皇权与相权之争,是一个皇权逐渐集中、相权逐渐式微的过程。(这是个体在“对完整权力渴望”的驱动之下的必然产物)
这个趋势在唐代并不明显,那会还主要是世族大家当政,有用人的胆量和容人的气魄。自宋朝开始,因为有了“晚唐五代进士轻薄传下的一辈小家样读书人”,就开始担心这担心那,想把一切权力都握在皇族手中,开始吞并相权。
到了明代,朱元璋因为宰相胡维庸造反,直接就把宰相给废掉了。但宰相的工作还是要有人去做,因为皇帝无法一个人完成,于是就设了一个内阁,也就是皇帝的秘书处;任命一个内阁大学士,也就是秘书长,来实际行使宰相的职权。
但对文官集团而言,你一个秘书长,是皇权的私人顾问,凭什么对我们政府组织指指点点的?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,即使是当时张居正这等极富才华与威望的秘书长,终因其名号的尴尬,也不得不发出“所处者危地,所理者皇上之事,所代者皇上之言”的感慨,最终被定性为“权臣弄权”,死后立马被抄家。
清朝沿袭了明代不设宰相的制度,内阁也开始搁置,转而设了个军机处:皇权吞并相权的同时,顺便把军事权力也集中到皇帝手中。
至此,皇权的集中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,平衡被彻底打破。
(三) 中间商赚差价
一种平衡一旦被打破,就势必会有另一股力量出现,试图重新达成一种新的平衡。皇权过于集中后,因凭大多数皇帝的一己之力,胜任皇权的治理范围都有困难,更不用说握皇权与相权于一手。
皇帝他也需要帮手啊。原来的帮手是宰相,宰相被边缘化了之后,宦官、外戚等与皇帝亲近的人,就有了作为中间商去赚差价的机会,真真实实地获得了一部分相权甚至一部分皇权。甚至到了明代,太监首领(司礼监)不仅成为了真宰相,而且是真皇帝。虽然明太祖朱元璋基于自身的高瞻远瞩,立下了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”的祖训,但却无法保证自己的子孙后代都像他一样勤奋、铁血且精力旺盛。
于是乎,皇权外落,有名无实。到头来,竟是为他人做嫁衣裳。
三
“读书人的政府”和书籍资本
书中自有颜如玉,书中自有黄金屋
因为汉代开始用举孝廉的制度,认认真真地选拔有学识的读书人做官、加入国家政权组织,并且“自汉武帝以后,汉代的做官人渐渐变成都是读书出身了”,钱穆先生把这种现象称之为“读书人的政府”,或者“士人政府”。
这一制度也缔造了中国人民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传统信念。到目前为止,我们政府组织中的人员,也都是以读书人为主,大部分人员都是经过各种考试制度层层选拔出来的。这就是“学而优则仕”。
在这种制度和信念的驱动之下,举国上下的人民都把读书奉为一件至高无上的事情,什么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,什么“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”。
不过在唐代之前,这个书,不是你想读就能随便读的。囿于当时造纸技术未成形、印刷技术未发明,书籍这个东西,可是很贵的。
根据钱穆先生描述,“古代书本必得传抄,一片竹简只能写二十来字。抄一本,费就大了。帛是丝织品,其贵更可知。而且要抄一本书,必得不远千里寻师访求”。可见在当时读书,不仅书籍成本高,获得知识的成本也很高。(人家说的学富五车,如果以竹简作为计量单位并换算成现在的纸质书籍的话,可能都装不满一行书架。据说学富五车只有“四十回《红楼梦》的字数”,这个说法笔者没有仔细考证,读者朋友们不必当真。不过庄子当年是用“学富五车”这个词来讽刺惠施的,只不过被后人用作了褒义。)
所以在纸张和印刷术推广之前,书籍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。而当时虽然已经不再是爵位世袭的年代,但书籍却是可以世袭的。于是乎,在读书人政府的背景下,书籍和知识“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”,并有“黄金满籝,不如遗子一经”一说。(那个不认识的字,读音同“赢”)
在古代中国,书籍也是一种资本。在这种书籍资本的加持下,“当时一个读书家庭,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,而同时便是有钱有势的家庭”。所以宋真宗赵恒再劝世人多读书时说“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”,放在当时的背景环境中来看,是一点也不假的。
不过说来也奇怪,宋真宗竟然把读书的目的仅仅锚定为“颜如玉”和“黄金屋”,未免漏掉了许多读书的乐趣。或许自有他政治宣传的考量。
四
用人的艺术
不但要画饼,还要能充饥
(一) 画饼的艺术
话说唐朝初期依赖于府兵制,开疆拓土,盛极一时。后来府兵制逐渐式微,朝代也开始走下坡路。这其中的原因,抛开当时配套的经济制度不谈,我们来看看用人方面的变化。
唐朝初期,只有上三等、中三等的民户子弟才可以当兵(唐朝根据各家财富产业,把民众分为九等),也就是穷人家的子弟,想当兵都当不了。
每个府兵都需要去中央首都服役一年(他们叫“上番”),此间或许还能跟李世民一起练习射箭。如果战死沙场了,中央政府收到军队上报的死亡名册后,会立即要求地方政府派人去死者家中慰问,赐予勋爵和赏赐。“阵亡军人的棺木还没运回,而政府一应抚恤褒奖工作都已办妥了”。
政府的这种做事方式,给了当时的军队以极大的精神鼓励。所以军队在战争中屡获胜果,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
但是从唐朝中期开始,因为开疆拓土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,国家对精壮兵力的需求量下降,府兵上番时就逐渐怠于操练,变得无事可做。
有剩余的劳动力,自然是不用白不用。于是乎,府兵上番期间,逐渐变成皇族亲贵修花园、盖房子时借用的苦工。
这样一来,军人有勋位在身的同时,却还要被唤去服力役,勋位开始转为一种羞辱,最终演变为“别人称呼你勋位如中尉、上校之类,已不是一种尊敬,而成了一种讥讽”,军人的地位开始下降。
式微,式微,胡不归?
随着军队内部管理风格的散漫,对战亡军人的抚恤工作也开始懈怠,以至于战事已经结束了、死者家属已经从私下渠道得知死讯了,而官方的抚恤慰问还迟迟不来。这样一来,在死者家属看来,“死的似乎白死了”,人心就开始涣散。
再加上府兵制后来变成没有复员的安排,要一辈子当兵,“归来白头还戍边”。而且是做苦力、没地位,府兵自带的绢帛钱财还会被抢夺。以上种种原因的催化之下,府兵制最终瓦解。
看来,把“希望”与“荣誉”作为用人的激励机制,很重要。
(二) 光画饼没用,还要能充饥
因为科举制度的盛行,唐朝政权对知识分子开放后,越来越多的读书人通过考试进入政府。当供过于求的时候,读书人开始变成“政治脂肪”。但当时政府的思路并不是减肥,而是找地方存放这些“脂肪”。
于是乎,唐朝的地方组织结构抛弃了汉代的扁平结构,开始增加层级:把县分上中下三级、把州也分上中下三级,这样一来,能安排的官员就增加了。
人员安排的问题是解决了,但是弊端也随之而来。
因为唐代的官员任用权全部集中于中央的吏部,政府只能以升迁来奖励地方官员。在汉代的扁平结构下,县官之上就是郡官,郡官的待遇已经等同于中央的三公九卿。这种情况下,因为阶级少,官员的升迁机会优越,故能各安其事,人事变动不大,行政效率也随之提高。
到了唐朝,光是县官就得内部先升3级,才能实质性地往上迈一级,升了等于没升。而唐朝的职事官有九品30级、散官有九品29阶。长此以往,虽然官员一直在升迁,但“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,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”。于是乎,官品中逐渐分清浊,官员与官员的地位开始有高低之分。而大批官员们也因为没有希望、没有动力,行政效率大幅下降。
这种状况一直持续,待到了明朝,明成祖一句“胥吏不能当御史”、“胥吏不能考进士”,便彻底坐实了流品的弊端。于是乎,师爷这个群体愈发兴盛,更从师爷唱主角的“胥吏政治”之中演化出“文书政治”(文书政治可以大约理解为:无字无真相,书面文件是第一生产力)。
行政环节中的各种繁文缛节、看不到希望的浊流群体的自暴自弃,一直在影响着行政效率,不停地制造问题(“流品”就是官阶,把官员分成优等和劣等,后来泛指人的社会地位、门第)。果真是,坏的制度让好人不能做好事。
可见用人这件事情,光画饼是不行的,画的饼还得能够充饥。不然,劳动者们醒悟过来只是迟早的事情。至于想靠画饼收割短期劳动力的,另说。但那有损用人者的风评,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
五
监察常驻
中央和地方的微妙关系
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向来都是微妙的,需要谨慎平衡。
(一) 中央与地方的角逐
中央对地方管得太死了吧,地方失去了自身发展的活力,中央也累得慌,根本管不过来。中央管太松了吧,地方就开始肆意妄为、欺上瞒下,甚至占山为王,向中央权威挑战。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历朝的通用做法是向地方派出监察人员(监察制度这个事情后面还要细说),并完善地方与中央的信息沟通机制,建立固定的地方信息上报制度。古代的修驿站、修官路,就有加快中央与地方间信息传递速度的考虑。
到了元朝,更是从地理的角度出发,把各省的地理界线划分得弯弯绕绕的,就是刻意把重要的地理防御工事分布在2个省、3个省甚至更多省份之中,防止其中某一个省依赖地理优势,难以被攻克。用钱穆先生的话说,“好使全国各省,都成支离破碎。既不能统一反抗,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”。(插播一句:行省制度是元朝开始启用的)
后代统治者自然明白元朝对地方行政区域划分方式的良苦用心,就传承了下来,并且一直沿用至今。不得不说,元代统治者对地理知识的娴熟运用,值得我们学习。
而元朝统治者对地理知识的重视,恐怕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宋代的惨痛教训:
北宋定都河南开封,黄河边,一大片平地。“骑兵从北南下,几天就可到黄河边。一渡黄河,即达开封城门下”,完全没有国防(自然,宋太祖这么做决定,有他的苦衷:当时承接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,国防线早已残破。宋朝需要养兵,养兵则需长江流域的粮食供给。如果定都洛阳或西安,运费太高了,国家财力负担不起)。
再加之开国宋太祖的弟弟宋太宗,两次对辽亲征都打了败仗,在这种没有国防的地理设定之下,宋朝不得不做好随时应战的准备。所以只能养兵,不能裁兵,还不能让军队复员。但同时,惮于祖先战败的惨痛教训,一朝被蛇咬,宋代也不敢再和北方辽国交战。最后养兵而不敢用兵,开销过大,最终死于积贫积弱。
看来,地理学知识的运用范围,比想象中的更广泛。扯远了,回到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制度。
(二) 监察常驻的危害
自秦汉以来,监察制度就已经是一种常态化的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制度,旨在监督中央指令在地方的执行情况,毕竟天高皇帝远。另外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中央集权,不想让地方的权力过分强大。
汉代设的中央特派员叫“刺史”,唐代的叫“监察使”、“观察使”(派去边疆的叫“节度使”),宋代的叫“监司”,明代叫“总督”、“巡抚”,清代叫“经略大臣”、“参赞大臣”。
那么问题来了:为什么每个朝代的中央特派员,都要换一个名字?是因为改朝换代了,中央特派员的名字也需要标新立异吗?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
其实,唐代也是有汉代“刺史”的,而宋代也有唐代的“观察使”,清代也有明代的“总督、巡抚”。那为什么不继续沿用上一个朝代的职责呢?因为上一个朝代派出的中央特派员,随着时间的推移,无一例外地都成了当地的行政首脑。汉代的特派员“刺史”,在唐代已经是一州的行政首脑,唐代的监察人员“观察使”是宋代的地方行政首长,明代的特派员“总督、巡抚”到了清代,也成了地方行政首脑。甚至唐代派往边疆的节度使,慢慢地也成为了边疆地区的首脑,自立山头,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,引发动乱,最终把唐朝消灭。清代也是如此。
为什么历史总是如此惊人的相似?因为监察人员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地方时,本身是带着至高的权力去的,因为他代表的是中央。既然钦差大臣来了,那地方遇到重要的事情,就得向钦差大臣汇报,并最终听钦差大臣的指挥。监察员一旦在地方驻扎的时间长了,这种自带的更高权力就会影响到地方的既有权力格局。久而久之,中央特派员就逐渐成为了地方的行政首脑。如果让中央特派员掌握地方军权,就更要命(请自行代入唐朝和清朝)。
一旦中央特派员成为地方首脑了,利益格局就变化了,最初的监察职责也就名存实亡,所以后朝只能再派新的中央特派员。如此循环往复。
由此可见,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机制,是需要经过精妙设计的。反观现在,监察人员要轮换值班,国企中的委派监事不能连任,多多少少有这方面的考虑。
六
文官武官,终归田园
农村大后方对国家政权稳定的保障
历代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传统,是不曾断绝的。但是仕途有通畅就有不畅。仕途不畅时,官员们该去往何方呢?
陶渊明说,田园将芜胡不归?“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基础,一向安放在农村”。大不了回家种田,是写入中华文明基因里的观念。所以我们常常看到,历代文官仕途不顺时,往往会请辞:回家种田,做个小地主,对外可以称之为“衣锦还乡”。唐朝的武官,因为空有勋号而无实职,除了在当朝做大将军的,剩下的也多是回家种田。有知识或有武力值的官员们在失意时有了情绪出口之后,就不会惹出太多幺蛾子。
基于中华文明的这种经济与文化基因,农村大后方在国家政权稳定方面,也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根据温铁军先生的观点,农村作为一个吸纳城市剩余劳动力的场所,在国家面临经济危机时,是一个重要的缓冲地带,并给国家度过经济危机提供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的支持,从而使局面趋于稳定。
所以国家为什么历来重视三农问题,是有原因的。
七
药以治病,亦以起病
不忘初心很重要
(一) 九品中正制的兴与败
话说东汉末年,汉献帝逃亡,中央与地方失联,察举制这一人才选拔制度也失去了施行的机构基础。于是朝廷用人时便失去了标准,文人领域还尚可控制,武人领域一片混乱,用人全凭在位者的喜好,良莠不齐。为了解决这一混乱,曹操任命陈群改革人事制度。陈群不负重任,基于当时的局面,创设了九品中正制。
所谓的“九品”,就是把人才分为“上上、上中、上下/中上、中中、中下/下上、下中,下下”九个层级。那么,由谁来做这个分类的工作呢?那就是“中正”(既中立又公正,才能担此重任)。
那这个“中正”又是怎么产生的呢?还是采用察举制的老方案:“就当时在中央任职,德名俱高者,由各州郡分别公推大中正一人”,也就是在各地方挑选一位他们在中央任职的、德行和名望都很高的官员,担任“大中正”。然后“大中正”再指定一名“小中正”,两位中正就负责他们所在地方州郡的人才评分工作。
评分标准有两个:一是能力,二是品行。被评价的对象:不仅包括未入官场的人员,也包括在职官员,旨在撤掉当时已经滥用的在职官员。评分的主要依据:地方的群众舆论和公共意见(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)。
打完分之后,中正就把评分册子上交吏部,吏部根据这套评分册子,再来决定在任官员的升迁、在野人才的聘用。这样就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客观的评价标准,解决了之前用人混乱的局面。这一套用人制度,对曹家初步统一天下是有所助益的。
但何以这一前朝治病的良药,成了后朝致病的毒药呢?因为每一种制度的施行,都对人们的后续行为有引导作用。
我们不妨再回过头去看看这个制度:
1. 中正对人才评分的标准是群众的意见,也就是“舆论”。而群众的眼睛当真是雪亮的吗?至少勒庞并不这么认为。
在《乌合之众》中,勒庞的观点是,群体只有形象思维,缺乏逻辑推理能力,“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。群体所接受的判断,仅仅是强加给他们的判断,而绝不是经过讨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”。这一观点读者们是否认同,暂且不论,我们且来看看当时的人们在这种制度的引导下,做出了什么行为:
因为人才评价重社会舆论,做官的人就“袭取社会名誉,却不管自己本官职务与实际工作”。因为人才评价机制在于听取社会舆论的“中正”,而真正了解官员业务能力及人品的上司,却无法把他们对下级官员能力与德行的评价发布出去。后果可想而知:慢慢地,官员们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经营自己的对外“人设”上。至于他的本职工作做得如何,没有人关心,也没有人知道;知道的人也难以把他们的观点扩散。
2. 大中正这个职位设在中央,而人才们想要大中正品题提拔自己,就纷纷往中央的大中正身边靠拢(所谓“认知”,要先“认”,才能“识”)。如此一来,人才纷纷往中央集中,地方缺乏人才可用,并导致地方的行政效率、风俗易化的脚步,都慢了下来。
至此,九品中正制已经完全异化,不仅不再具有其初设时分清定浊的作用,反而给人才选拔带来不便,给世人的行为举止产生的不良的引导,最终被后世唾弃,并被唐朝的科举考试制度取代。
之所以有这种局面,就是因为后朝没有去思考前朝推行这一制度的背景和原因,在时代背景变化之后仍然一味沿用,终致当初“治病之良药”,变成了现在的“致病之毒药”。
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
【想起一个小故事:军营操场中的某把铁椅,常年以来都有2名士兵把守,但不知原委,都是奉命行事。一日,退休的长官到访,见到这把椅子依然有人把守,便问左右随同:30年了,这把椅子上的油漆还没有干吗?】
(二) 从“租庸调”到“两税制”
无独有偶,唐代的税收制度,也经历了从“良药”到“毒药”的转变。
唐初为了从战乱中恢复元气,轻徭薄赋、为民制产,推行“租庸调”的税收制度,让有恒产者有恒心。这是一种计划经济时代的属人税收制度:
所谓“租”,你可以大致理解为“土地承包制+农业税”: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,人丁年满18岁时官方授予他一定面积的田地;满60岁时把田地交换国家。耕种期间,每年按2.5%的税率(四十税一)向国家缴纳农业税。
所谓“庸”,是一种力役,每个成年人丁每年向国家提供20天的义务劳动。
所谓“调”,是一种特产税,各地人民每年需要向中央贡献一定量的当地土产,以丝麻织物为主。
这一套制度下来,形成了“有田始有租,有身始有庸,有家始有调”的格局,旨在为民制产,达到“有恒产者有恒心”的目的。而按人头分配一定面积的田地,也具有一定计划经济的属性,试图通过“均田地”实现“天下大同”(大约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倡导的共同富裕)的终极政治理想。
那么这一税制的实施效果如何呢?
既然要属人管辖,租庸调这一税制的根基,便是人口户籍管理制度,他们当时称“账籍”制度。“账”是壮丁册,一年一刷新;“籍”是户口册,三年一刷新。也就是在唐代,每1年要做一次壮丁普查,每3年要做一次全民人口普查。人口普查这件事情,在数据和技术均完备的现在,开展起来尚是纷繁复杂;那在车马皆慢的唐朝,其难度可想而知。而人类这个物种,往往是喜欢偷懒的,时间久了就开始懈怠:年过60的壮丁不销户,满18岁的新丁没增名,已经去世的人没有及时从户口本中删除,新授予的田地没有及时修改权利主体……更有地方豪强从中舞弊、阻挠制度施行。如此种种,最终导致户口登记逐渐错乱,“账籍”制度无法推行,并成为租庸调制失败的最大原因。
对此,钱穆先生总结的应对之道是:“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,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。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,纵然良法美意,纵是徒然。”
所以,历代王朝为何推荐儒家/法家/道家思想,各种组织为何强调统一思想,各家企业为何建立企业文化,每个家庭为何开展家风建设,都是同样的道理。人类喜欢听故事,人类也需要听故事。
租庸调制失败后,两税制开始登场,并开启了唐朝的自由经济时代。
所谓“两税”,就是两次征税:夏天征一次,秋天征一次。与租庸调制不同,两税制是一种属地的税收制度:谁在这片土地上居住不重要,把该交的税交上来就行。这样一来,人口不再受户口的牵制,人口流动变得自由。
但这自由的代价,便是土地兼并:之前的租庸调制是按人口分配田地的,现在田地不按人头分配了,土地的流通就是可以允许的。而历朝历代的土地兼并,最终的后果总是贫者愈贫、富者愈富,最终导致地方割据、各占一方(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)。唐朝也不例外。
随着实施时间拉长,两税制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弊端:最初将租庸调改两税制,还有简化手续之考虑,把原来的3个税种放入土地中一并征收。但是慢慢的,主政者就忘了当初的那个设定,忘了初心,觉得税收不够用时,又巧立名目,新增征税项目。“而这些新项目,本来早就有的,只已并在两税中征收了;现在再把此项目加入,岂不是等于加倍征收!这是税收项目不分明之弊。”这样一来,民众的税赋自然就重了。
再者,两税制采属地管辖,税基按该政策出台前一年的税收金额来定,后续不再调整。不管这个地区人口多寡、年度收成好坏,都要交固定金额的税。税收“变成了一种硬性规定,随地摊派,而不再有全国一致的租额和税率了”。如果某一地区某年收成不佳,或者其他偶发原因导致经常居住人口减少,在税收总额不变的情况下,剩下居民的税赋就会加重。而单位数量人口的生产力是有限的,税赋一重,居民负担不起,就会往税赋低的地区迁徙;如此一来,剩下居民的税赋会更重。循环往复。
此外,唐朝两税制不是纳粮,而是纳银(货币)。农民必须卖粮换钱,用来交税。有交易,就会有中间商赚差价。最终被市场调节的,还是底层供货商——农民。
因为有这些弊端,两税制的推行,失去了“为民制产”的初衷,引发土地兼并和贫富不均,而且实质上是在奖励地主的剥削,最终为唐朝末期的农民起义埋下了祸根。
八
兴替间的传承
现有制度中的历史厚重感
在阅读历史的过程中,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现有制度中的历史厚重感的。中国古人的传统智慧,仍然在指导着我们现在的生活。这里难以列举齐全,稍微举一些例子:
(一) 按各区人口比例,分配人才的录用名额
从汉代开始,人才的选拔制度便是分区定额的:根据各地区人口基数的不同,分配不同比例的人才录取额度。为的是平衡各地区的利益,听到各地区的声音。这个制度,一直沿用至今,具体体现在高考时各省的录取人数、以及因此形成的各地高考难度不一的现象。
(二) 联席会议制度、联动办公制度
唐朝的三省因相互制约,一道政令出台前需要三省交叉审核。为了提升行政效率,政府需要制定行政命令时,门下省和中书省便会举办联席会议,共同审核政令。这一制度也沿用至今,且广泛存在于政企的各部门协调工作之中。
此外,唐朝六部因共有24司,为了实现协同办公,每天上午各部主管都在都堂集体办公。这可能是我们现在政府各部门联动办公的原型。
(三) 公务员不得经商
汉朝就规定,商人不能做官,做官人不能经商。到了唐朝,直接从报考资格开始限定:工商界人士不能参加科举考试,“因为商人是专为私家谋利的,现在所考试求取者则须专心为公家服务”,更不能有犯罪记录。这就是所谓的“身家清白”。这一制度也是沿用至今,公务员不得经商。
另外,还有前两篇提到的国家对特定行业的专营制度、学而优则仕的传统、各省行政区域的划分、监察制度、三农政策、户籍制度、人口普查制度等等,都是传袭于唐汉甚至更早的年代。再如宋代的匿名评卷制度、元代的中央特派员制度、历朝以来形成的文书政治、士人政权的传统,都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。传统文化中的智慧,是值得我们学习并发扬光大的。
九
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
成年人不应回过头嘲笑蹒跚学步的孩童
钱穆先生历来主张以温情的眼光去看待历史。“制度决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,而系从现实中产生者。惟此种现实中所产生之此项制度,则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论与精神。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,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。”
任何一项制度的产生,都是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现实土壤,都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。如果不代入当时的现实环境,而是以后来的眼光去评价一项制度的得失,是不合适的(这也是“事后诸葛亮”不招人喜欢的主要原因)。
作为一个成年人,在学会了走路之后,如果再去嘲笑孩童时的蹒跚学步,也是不合适的。当然,根据制度制定者的前瞻性、周全性、经验丰富程度的差异,不同的制度本身依旧有其优劣之分。
笔者只能说:前世之事,后世之师。
作者简介
李芳
国浩深圳合伙人
业务领域: 建设工程与房地产、投资与并购、民商事争议解决
邮箱:lifangsz@grandall.com.cn

